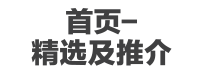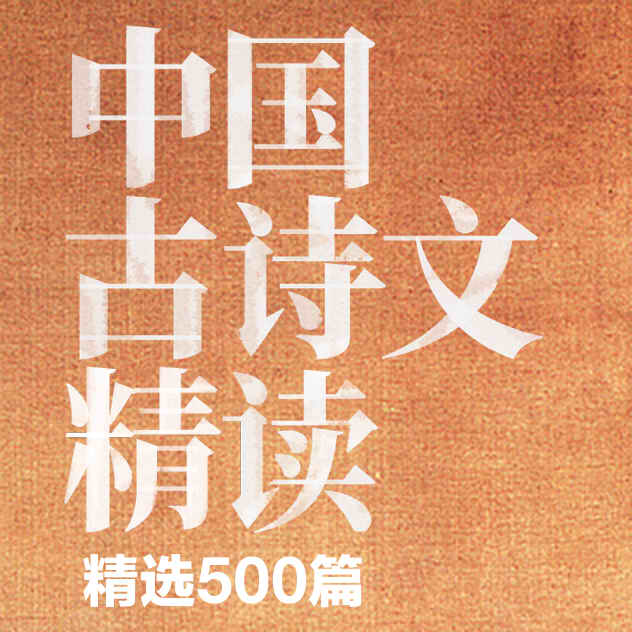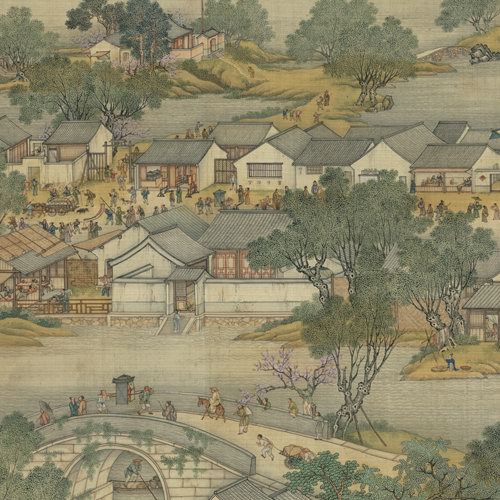齐桓晋文之事章
孟子对曰︰「仲尼之徒,无道桓、文之事者,是以后世无传焉,臣未之闻也;无以,则王乎?」孟子对曰:「仲尼3之徒,无道桓、文之事者,是以后世无传焉,臣未之闻也;无以4,则王5乎?」
孟子答:「仲尼的信徒,没有谁称道桓、文的事业的,因此,后代没有传授下来。臣也没有听说过;如果硬要我说下去的话,还是谈谈王道好吗?」
曰︰「德何如,则可以王矣?」曰:「德何如,则可以王矣?」
问:「德行要怎么样,才能够成功王业?」
曰︰「保民而王,莫之能御也。」曰:「保民而王,莫之能御也。」
答:「用保养人民做王业的基础,谁也抵挡不住。」
曰︰「若寡人者,可以保民乎哉?」曰:「若寡人者,可以保民乎哉?」
问:「像寡人这样的人,也可以保养人民吗?」
曰︰「可。」曰:「可。」
答:「可以。」
曰︰「何由知吾可也?」曰:「何由知吾可也?」
问:「怎么知道我可以呢?」
曰︰「臣闻之胡龁曰︰王坐于堂上,有牵牛而过堂下者,王见之,曰︰『牛何之?』对曰︰『将以衅钟。』王曰︰『舍之。吾不忍其觳觫,若无罪而就死地。』对曰︰『然则废衅钟与?』曰︰『何可废也?以羊易之。』不识有诸?」曰:「臣闻之胡龁6曰:王坐于堂上,有牵牛而过堂下者,王见之,曰:『牛何之?』对曰:『将以衅钟7。』王曰:『舍8之。吾不忍其觳觫9,若无罪而就死地。』对曰:『然则废衅钟与?』曰:『何可废也?以羊易之。』不识有诸10?」
孟子说:「臣听胡龁说过,有一次王坐在大堂上,有个牵牛的走过堂下,王见了就说:『牛牵去哪里?』答道:『准备用来衅钟。』王说:『放了牠!我不忍看牠混身抖颤,像没犯罪给执行死刑的样子。』答道:『那末,不要衅钟了吗?』王说:『怎么可以不?换只羊来。』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?」
曰︰「有之。」曰:「有之。」
王答:「有的。」
曰︰「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为爱也,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」曰:「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为爱也,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」
孟子说:「凭这点心肠便足够开创王业了。一般老百姓还以为大王小气呢,臣却知道是大王的不忍啦。」
王曰︰「然;诚有百姓者。齐国虽褊小,吾何爱一牛,即不忍其觳觫,若无罪而就死地,故以羊易之也。」王曰:「然;诚有百姓者。齐国虽褊11小,吾何爱一牛,即不忍其觳觫,若无罪而就死地,故以羊易之也。」
王说:「对的,只要真有百姓的话,齐国纵然狭小,我何至于吝惜一头牛?确是不忍心看牠混身抖颤,像没犯罪给执行死刑的样子,所以才叫用羊来换掉牠。」
曰︰「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。以小易大,彼恶知之?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,则牛羊何择焉?」曰:「王无异12于百姓之以王为爱13也。以小易大14,彼恶15知之?王若隐16其无罪而就死地,则牛羊何择焉?」
孟子说:「大王也别怪老百姓以为大王是小气。他们只看到用小的羊掉换大的牛,王这一片苦心,他们哪里能懂得?不过,大王如果只是可怜那没犯罪去给执行死刑的动物,那末,牛羊又有甚么分别呢?」
王笑曰︰「是诚何心哉!我非爱其财,而易之以羊也,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。」曰︰「无伤也。是乃仁术也,见牛未见羊也。君子之于禽兽也,见其生,不忍见其死;闻其声,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」王笑曰:「是诚何心哉!我非爱其财17,而易之以羊也,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。」曰:「无伤也。是乃仁术18也,见牛未见羊也。君子之于禽兽也,见其生,不忍见其死;闻其声,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」
王笑道:「真是呢,我那时也不懂是一种甚么心理!但我的确不是为了牛的价值比羊的大,才想到用羊换掉牛的;怪不得老百姓要以为我小气了。」孟子说:「不要紧的。这正是推行仁政的心理基础呢,因为当时只看见牛怕死的样儿而并没看见羊。大凡君子对于禽兽,原是看见牠的生,便不忍再看牠的死;听见牠的叫,便不忍再吃牠的肉的;所以君子总是不大进厨房的。」
王说曰︰「『诗』云︰『他人有心;予忖度之。』夫子之谓也。夫我乃行之,反而求之,不得吾心;夫子言之,于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,何也?」曰︰「有复于王者曰︰『吾力足以举百钧,而不足以举一羽;明足以察秋毫之末,而不见舆薪。』则王许之乎?」曰︰「否。」王说曰:「『诗』19云:『他人有心;予忖度20之。』夫子之谓也。夫我乃行之,反而求之,不得吾心;夫子言之,于我心有戚戚21焉。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,何也?」曰:「有复于王者曰:『吾力足以举百钧22,而不足以举一羽;明足以察秋毫之末23,而不见舆薪24。』则王许之乎?」曰:「否。」
王听了高兴地说:「《诗经》上说:『别人的心事,我会揣度得到』;这两句简直就是对您老先生说的了。因为本是我自己做的事,回头一研究,自己心里不得劲;经老先生这么一说,便直打在我心坎里了。不过这种心理所以和王道相合的缘故,又是怎样呢?」孟子答道:「假使有人告诉大王说:『我的力量能够举起三千斤,但却不能举起一根羽毛;目力能够看清秋毫的末梢,但却看不清一车木柴。』这种话大王能相信吗?」王说:「不。」
「今恩足以及禽兽,而功不至于百姓者,独何与?然则一羽之不举,为不用力焉;舆薪之不见,为不用明焉;百姓之不见保,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,不为也,非不能也。」「今恩足以及禽兽,而功不至于百姓者,独何与25?然则一羽之不举,为不用力焉;舆薪之不见,为不用明焉;百姓之不见保,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,不为也,非不能也。」
「那末,如今恩泽能够加到禽兽身上,可是功效却反不能达到百姓头上,这是甚么道理?足见一根羽毛举不起,只是不肯用腕力罢了;一车木柴看不清,只是不肯用目力罢了;老百姓没有受到保养,只是不肯用恩泽罢了。所以大王的不能建立王道政治,只是不肯做,并不是不能做。」
曰︰「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?」曰:「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?」
王问:「不肯做和不能做的情形有甚么不同?」
曰︰「挟太山以超北海,语人曰,『我不能』;是诚不能也。为长者折枝,语人曰,『我不能』;是不为也,非不能也,故王之不王,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;王之不王,是折枝之类也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以及人之幼;天下可运于掌。《诗》云︰『刑于寡妻,至于兄弟,以御于家邦。』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,足以保四海;不推恩,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,无他焉,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兽,而功不至于百姓者,独何与?权然后知轻重,度然后知长短;物皆然,心为甚;王请度之。……」曰:「挟太山以超北海26,语人曰,『我不能』;是诚不能也。为长者折枝27,语人曰,『我不能』;是不为也,非不能也,故王之不王,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;王之不王,是折枝之类也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28;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9;天下可运于掌。《诗》云:『刑于寡妻,至于兄弟,以御于家邦。』30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,足以保四海;不推恩,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,无他焉,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兽,而功不至于百姓者,独何与?权31然后知轻重,度32然后知长短;物皆然,心为甚;王请度之。……」
孟子答:「譬如要一个人挟着泰山跳过北海,那人告诉人说:『我不能;』这真的是不能。要一个人给长辈按摩,那人告诉人说:『我不能;』这便是不肯,并不是不能。所以大王的不能建立王道政治,并不是挟着泰山跳过北海的一类;大王的不能建立王道政治,只不过是替长辈按摩的一类。老实说,只消把侍奉自己老辈的心情去加到人家的老辈头上,把爱护自己小辈的心情去加到人家的小辈头上,便天下都可以握到手掌心里了。《诗经》里说:『先做榜样给妻房,再到兄弟行,步步推行到家邦。』意思即是说把我这颗心让它在我以外的人们身上起作用罢啦。所以能够推广恩泽,便能够保养四海;不能够推广恩泽,便结果连妻室儿女都要会保养不了。古时候的人所以大大地超过现代人的地方,并没有别的,只是善于推广他们的行为影响罢了。如今恩泽能够加到禽兽身上,可是功效反而不能达到百姓头上,这是甚么道理?称过以后才知道轻重,量过以后才知道长短;物理都是这样,心理尤其是这样;还请大王考虑。……」
导赏
实行王道政治,就是孟子的政治主张,同时也可以说是儒家的政治主张。本文是因齐宣王以齐桓、晋文之事问孟子,才引出孟子一大段讲王道的议论。这里孟子所说的意思,在阐明王道推行甚易,问题只是统治者不肯做,并非不能做,藉以鼓励齐宣王放弃霸道的幻想,而改行王道政治。全用具体的比喻,阐发抽象的道理;先秦诸子,惯用此法,孟子尤甚。本篇目的在劝齐宣王行王道,却先贬低桓、文的霸道,以抬高王道的价值。再说王道并不难懂,仅一点不忍之心便「足以王」。最后说王道并不难行,只是人君不肯行,而非不能行。步步进逼,明白异常,亦痛快异常。
本文虽是纪述的两个人的对答,然而却是一种议论文的体裁,因为孟子在提出自己的主张,使对方信服。用问答体来发挥议论的,在先秦诸子的文章中很多;孟子这类的文章,实已开了以后策士论文的先河。
 延伸阅读:
延伸阅读:
查阅次数:6086
資料來源:
朗读:張敬才(粤)、程广宽(普)
|
注释、译文:《友联活叶文选》,友联出版社
|
导赏:《友联活叶文选》,友联出版社(文)、張敬才(粵)、程广宽(普)
作者/出处
《孟子》
《孟子》一书,有以为是孟子自撰,有以为是其门人所记,《汉书‧艺文志》列入儒家类,今存七篇。 宋以后列于经部,朱熹将它与《论语》、《礼记》的〈大学〉和〈中庸〉篇合成《四书》,为之作注,从此成儒家经典。
孟子,生于周烈王四年,卒于周赫王二十六年(公元前三七二──二八九)。 名轲,邹(今山东邹县)人,战国时代大思想家。 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,是继孔子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。 孟子身处战乱的时代,提倡「民贵君轻」,主张推行「王道」,可是不被诸侯所采纳,于是退而讲学著述。 《孟子》的文章,长于辩论,善用譬喻,气势磅礴,感情奔放,对后世散文有很大影响。 通行注本有东汉赵歧《孟子章句》、宋孙奭《孟子注疏》、朱熹《四书集注》和清焦循《孟子正义》。
查阅次数:6221
資料來源:
《中国文学古典精华》,商务印书馆(香港)有限公司
创作背景
本篇選自《孟子・梁惠王篇》;以內容乃孟子和齊宣王的問答,故特標今題。對,即對答的意思。
資料來源:
《友联活叶文选》,友联出版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