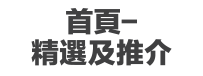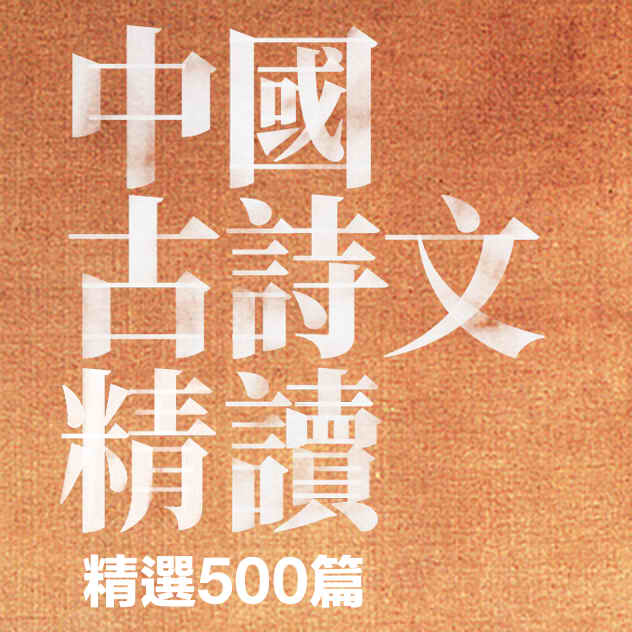與王介甫書
光居常無事,不敢涉兩府之門,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。春暖,伏維機政餘裕,台侯萬福。光居常無事,不敢涉兩府1之門,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2。春暖,伏維機政餘裕,台3侯萬福。
光平常沒有要緊的事情,不敢到中樞機關打擾,所以好久沒有謁見閣下。現在天氣回暖,敬祝政務從容、福德無量。
孔子曰︰「益者三友,損者三友。」光不材,不足以辱介甫為友。然自接侍以來,十有餘年,屢嘗同僚,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也。雖愧多聞,至於直諒,不敢不勉;若乃便佞,則固不敢為也。孔子曰:「益者三友,損者三友。」4光不材,不足以辱介甫為友。然自接侍以來,十有餘年,屢嘗同僚,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也。雖愧多聞,至於直諒,不敢不勉5;若乃便佞6,則固不敢為也。
孔子說:「益者三友,損者三友。」光不成材,不夠資格作介甫的朋友。不過自從會面以來,十幾年了,曾經數次同事,也不能說毫無情誼。雖然很慚愧說不上「多聞」,至於「直率」和「誠實」,不敢不勉力做到;如果說到巧言諂媚,那是我不敢做的。
孔子曰︰「君子和而不同;小人同而不和。」君子之道,出處語嘿,安可同也;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,輔世養民,此其所以和也。曏者,與介甫議論朝廷事,數相違,未知介甫之察不察;然於光嚮慕之心,未始變移也。孔子曰:「君子和而不同;小人同而不和。」7君子之道,出處語嘿8,安可同也;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,輔世養民,此其所以和也。曏者9,與介甫議論朝廷事,數相違,未知介甫之察不察;然於光嚮慕之心,未始變移也。孔子說:「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」君子立身於世,作一件事或不作一件事、說一句話或不說一句話,都是根據各人自己良心判斷,自然不會雷同;可是各人的志向都是要以頂天立地的人格推行自己的理想,輔助社會教養民眾,因此他們相處是和諧的。在過去和介甫討論朝廷政事的時候,意見常相違背,也不知介甫是否注意於此,不過就光來說,敬慕之心是從來沒有改變的。
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,才高而學富,難進而易退。遠近之士,識與不識,咸謂介甫不起而已,起則太平可立致,生民咸被其澤矣。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,引參大政,豈非亦欲望眾人之所望於介甫邪?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,才高而學富,難進而易退。遠近之士,識與不識,咸謂介甫不起而已,起則太平可立致,生民咸被其澤矣。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,引參大政,豈非亦欲望眾人之所望於介甫邪?
以光所見,介甫享有極為崇高的名望達三十餘年,才力強而學識富,很難請出而很易退休。遠近的人,不論是否相識,都說介甫不被起用則已,一起用就可以很快得到太平,使全國人民受到利益。因此天子在介甫不願被起用的情形下堅決起用介甫,加以重大的政務責任,這豈不是也對介甫懷有和眾人一樣的希望嗎?
今介甫從政始朞年,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,莫不非議介甫,如出一口;下至閭閻細民,小吏走卒,亦切切怨歎,人人歸咎於介甫。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?光竊意門下之士,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,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。非門下之士,則皆曰︰「彼方得君而專政,無為觸之以取禍;不若坐而待之,不過二三年,彼將自敗。」若是者,不唯不忠於介甫,亦不忠於朝廷。今介甫從政始朞年10,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,莫不非議介甫,如出一口;下至閭閻11細民,小吏走卒,亦切切怨歎,人人歸咎於介甫。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?光竊意門下之士,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,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。非門下之士,則皆曰:「彼方得君而專政,無為觸之以取禍;不若坐而待之,不過二三年,彼將自敗。」若是者,不唯不忠於介甫,亦不忠於朝廷。現在介甫從政不過一年,而讀書做官的人,不論是在朝廷的還是從各地來的,都一致批評介甫;下至普通百姓、小官小兵,也紛紛抱怨歎息,人人都責備介甫。不知介甫是否也曾聽到這些言論而明瞭其原故?以光推測,您手下的人員正在天天歌頌盛德,贊揚功績,恐怕沒有一個人敢把這些情形報告上去的。不是您手下的人員,則都說:「他正得皇上信任、專主政事,不必觸犯他而取得禍事;不如坐着等他,不過兩三年,他自己就倒合了。」像這樣的話,不只不忠於介甫,也不忠於朝廷。
若介甫果信此志,推而行之,及二三年,則朝廷之患已深矣,安可救乎?如光則不然,忝備交遊之末,不敢苟避譴怒,不為介甫一一陳之。若介甫果信此志,推而行之,及二三年,則朝廷之患已深矣,安可救乎?如光則不然,忝備交遊之末12,不敢苟避譴怒,不為介甫一一陳之。假如介甫果真對這方針有信心,推行下去,到兩三年以後,朝廷的禍患已經深重了,怎麼能挽救呢?至於光則不如此,既有榮幸相交,就不敢為了避免譴責加怒而不向介甫詳細陳述。
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,謗詆無所不至,光獨知其不然。介甫固大賢,其失在於用心太過,自信太厚而已。何以言之?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,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,委任而責成功也;其所以養民者,不過輕租稅,薄賦斂,已逋責也。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,不足為,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;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,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,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,使之講利。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,謗詆無所不至,光獨知其不然。介甫固大賢,其失在於用心太過,自信太厚而已。何以言之?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,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,委任而責成功也;其所以養民者,不過輕租稅,薄賦斂,已逋責13也。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,不足為,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;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14而自治之,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15,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,使之講利。
現在激烈反對介甫的人,攻擊詆譭無所不至;光則知道他們是錯了。介甫實際上是很正直的賢人,過失只是用心思太過,自信心太強而已。為甚麼這樣說呢?自古以來聖人賢人治理國家的辦法,不過是使百官各稱其職,委給任務,督責完成;養育民眾的辦法,不過是減輕租稅,薄收田賦,清理債務。介甫以為這都是迂腐書生的常談,不值得採納,一定要想出古人所沒有做過的事來做;於是財政經濟事務不交給原有的「三司」而自己掌管,新成立「制置三司條例司」,聚集一些文人和財經人員,讓他們研討營利之道。
孔子曰︰「君子喻於義,小人喻於利。」樊須請學稼,孔子猶鄙之,以為不知禮義信。況講商賈之末利乎?使彼誠君子邪,則固不能言利;彼誠小人邪,則固民是盡,以飽上之欲,又可從乎?是知條例一司,已不當置而置之。又於其中不次用人,往往暴得美官;於是言利之人,皆攘臂圜視,衒鬻爭進,各鬭智巧,以變更祖宗舊法。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,所得不能償其所亡;徒欲別出新意,以自為功名耳。此其為害已甚矣。孔子曰:「君子喻於義,小人喻於利。」16樊須請學稼,孔子猶鄙之,以為不知禮義信17。況講商賈之末利乎?使彼誠君子邪,則固不能言利;彼誠小人邪,則固民是盡,以飽上之欲,又可從乎?是知條例一司,已不當置而置之。又於其中不次用人,往往暴得美官;於是言利之人,皆攘臂圜視,衒鬻18爭進,各鬭智巧,以變更祖宗舊法。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,所得不能償其所亡;徒欲別出新意,以自為功名耳。此其為害已甚矣。孔子說:「君子喻於義,小人喻於利。」樊須要求學農事,孔子都看不起他,以為他不知禮義信之重要。何況講求經商營利的事嗎?如果這些人真是君子,則他們就不能討論營利;如果這些人是小人,則他們一定是盡量搾取人民來向上報功,又怎能聽從他們的話呢?由此可知,所設置的「條例司」這一機關,是不應當設置的。而在這機關中用人,又不按照規定辦法,往往一步登天得到大官作;於是講財利的人都磨拳擦掌,躍躍欲試,自賣自誇,爭取地位,千方百計地來變更祖宗舊法。一般說來,所造成的利益不能補足所造成的損害,都是得不償失,僅僅是別出心裁來謀取個人的功名而已。這種作法為害人民已經很厲害了。
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,使行新法於四方︰先散青苗錢,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,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。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,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,陵轢州縣,騷擾百姓者。於是士大夫不服,農商喪業。故謗議沸騰,怨嗟盈路。迹其本原,咸以此也。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19四十餘人,使行新法於四方:先散青苗錢20,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21,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22而行之。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,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,陵轢23州縣,騷擾百姓者。於是士大夫不服,農商喪業。故謗議沸騰,怨嗟盈路。迹其本原,咸以此也。而又設置「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」四十多人,使他們到各地去推行新法:先發「青苗錢」,接着又要每家每戶出「助役錢」,接着又要找些農田水利的事來作。派來的這些人雖然也都是選擇有才能的人,可是其中也有輕浮狂躁的人,在地方上作威作福,騷擾老百姓。於是讀書作官的人不服,農人商人都不能安居樂業。因此反對意見沸騰起來,怨嘆之聲充滿天下。推究其根原,都是由此而起。
《書》曰︰「民不靜,亦惟在王宮邦君室。」伊尹為阿衡,有一夫不獲其所,若己推而內之溝中。孔子曰︰「君子求諸己。」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,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。《書》曰:「民不靜,亦惟在王宮邦君室。」24伊尹為阿衡25,有一夫不獲其所,若己推而內之溝中26。孔子曰:「君子求諸己。」27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,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。《書經》說:「民不靜,亦惟在王宮邦君室。」伊尹作阿衡的時候,只要有一個人得不到適當照顧,伊尹就覺得好像是他自己把那人推到溝裏去的一樣。孔子說:「君子求諸己。」介甫也該自己想想造成目前情勢的原因,不可以專門歸罪給天下之人。
夫侵官者,亂政也,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;貸息錢,鄙事也,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;徭役自古皆從民出,介甫更欲斂民錢,雇市傭而使之。此三者,常人皆知其不可,而介甫獨以為可;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,直欲求非常之功,而忽常人之所知耳。夫侵官者,亂政也,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;貸息錢,鄙事也,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;徭役28自古皆從民出,介甫更欲斂29民錢,雇市傭而使之。此三者,常人皆知其不可,而介甫獨以為可;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,直欲求非常之功,而忽常人之所知耳。
侵犯職權,是昏亂的行政制度,而介甫認為是治理天下的好辦法,首先實施;貸欵取利,是卑鄙的事,而介甫認為是仁厚的政策,努力推行;自古以來,人民就給國家服勞役,而介甫要徵收人民的錢,另雇民工來作事。這三件事,平常人都知道不對,而介甫獨獨認為對;這並不是介甫的智識不及平常人,實在是因為要建立非常的功績,而忽略了平常人都有的知識。
夫皇極之道,施之於天地人,皆不可須臾離。故孔子曰︰「道之不明也,我知之矣︰智者過之;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行也,我知之矣︰賢者過之;不肖者不及也。」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;及其失也,乃與不及之患均。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。夫皇極之道30,施之於天地人,皆不可須臾31離。故孔子曰:「道之不明也,我知之矣:智者過之;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行也,我知之矣:賢者過之;不肖者不及也。」32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;及其失也,乃與不及之患均。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。不論天地人,都應當時時刻刻謹遵平正的中道。所以孔子說:「道之不明也,我知之矣:智者過之;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行也,我知之矣:賢者過之;不肖者不及也。」介甫的「智」與「賢」都超過常人;而一有過失,即與不及者的毛病相等。這就是光所謂用心太過的意思。
自古人臣之聖,無過周公與孔子,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,未嘗無師。介甫雖大賢,於周公、孔子,則有間矣。今乃自以我之所見,天下莫能及︰人之議論與我合,則善之;與我不合,則惡之。如此,方正之士何由進?諂諛之人何由遠?方正日疏,諂諛日親,而望萬事之得其宜,令名之施四遠,難矣!夫從諫納善,不獨人君為美也,於人臣亦然。自古人臣之聖,無過周公與孔子,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,未嘗無師。介甫雖大賢,於周公、孔子,則有間33矣。今乃自以我之所見,天下莫能及:人之議論與我合,則善之;與我不合,則惡之。如此,方正之士何由進?諂諛之人何由遠?方正日疏,諂諛日親,而望萬事之得其宜,令名之施四遠,難矣!夫從諫納善,不獨人君為美也,於人臣亦然。
自古作臣子的人,聖明沒有超過周公和孔子的,周公孔子也未嘗沒有過失、沒有師法。介甫雖然是大賢,和周公孔子相比,自然還有距離。現在卻自以為我的見解,天下不能及;別人的意見與我相合就認為是好的,與我不合就認為是壞的。這樣一來,正直的人怎能進用?諂媚的人怎能遠離?和正直的人越來越疏遠,和諂媚的人越來越親近,而希望萬事都做得恰當,希望四方遠處都聞知美名,那是很難了!聽取反對言論、採納良善意見,不僅是作君主的美德,作臣子的也是如此。
昔鄭人遊於鄉校,以議執政之善否,或謂子產毀鄉校,子產曰︰「其所善者,吾則行之;其所惡者,吾則改之。是吾師也,若之何毀之?」薳子馮為楚令尹,有寵於薳子者八人,皆無祿而多馬,申叔豫以子南、觀起之事警之;薳子懼,辭八人者,而後王安之。趙簡子有臣,曰周舍,好直諫,日有記,月有成,歲有效。昔鄭人遊於鄉校,以議執政之善否,或謂子產毀鄉校,子產曰:「其所善者,吾則行之;其所惡者,吾則改之。是吾師也,若之何毀之?」34薳子馮為楚令尹,有寵於薳子者八人,皆無祿而多馬,申叔豫以子南、觀起之事警之;薳子懼,辭八人者,而後王安之35。趙簡子有臣,曰周舍,好直諫,日有記,月有成,歲有效。從前鄭國人在鄉校聚會,議論執政者的是非,有人勸子產把鄉校毀掉,子產說:「他們贊成的事,我就實行;他們反對的事,我就改正。這是我的導師,為甚麼要毀掉它?」薳子馮作楚國令尹,他所寵愛的有八個人,都不是正式官員,可是養了許多馬;申叔豫就以子南和觀起的事為例,向他提出警告,薳子警惕,把那八人打發走,然後國王才對他放心。趙簡子有一個家臣,叫周舍,喜歡直諫,對趙簡子的過失每天有記錄,每月有一次總結,每年有一次全面檢討。
周舍死,簡子臨朝而歎曰︰「千羊之皮,不如一狐之腋。諸大夫朝,徒聞唯唯,不聞周舍之諤諤,吾是以憂也。」子路,人告之以有過則喜。酇文終侯相漢,有書過之史。諸葛孔明相蜀,發教與群下,曰︰「違覆而得中,猶棄敝蹻而獲珠玉。然人心苦不能盡;惟董幼宰參畫七年,事有不至,至於十反。」周舍死,簡子臨朝而歎曰:「千羊之皮,不如一狐之腋。諸大夫朝,徒聞唯唯,不聞周舍之諤諤,吾是以憂也。」36子路,人告之以有過則喜37。酇文終侯38相漢,有書過之史。諸葛孔明相蜀,發教與群下,曰:「違覆而得中39,猶棄敝蹻40而獲珠玉。然人心苦不能盡;惟董幼宰41參畫七年,事有不至,至於十反。」周舍死後,簡子坐朝時歎息道:「千張羊皮也不及一張狐皮司貴。諸位大夫朝見,我只聽到唯唯諾諾的,而聽不到周舍那種直率的意見,真使我因此發怒。」子路的為人,別人告訴他犯有甚麼過失,他就很喜歡。蕭何作漢朝相國,專門委派人記載他的過錯。諸葛孔明作蜀國的丞相,對下級發出教令說:「經過下級的商榷反映,而得到適當的辦法,就像丟掉破鞋而得到珠玉一樣可喜。可是問題在有些人不肯盡心。只有董幼宰,在他參預政事的七年內,有時為了一件事未達盡善盡美,他會反覆提出十次之多。」
孔明嘗自校簿書,主簿楊顒諫曰︰「為治有體,上下不可相侵。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;今有人,使奴執耕稼,婢典炊爨,雞主司晨,犬主吠盜,私業無曠,所求皆足。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,不復付任,形疲神困,終無一成。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?失為家主之法也。」孔明謝之。及顒卒,孔明垂泣三日。孔明嘗自校簿書,主簿楊顒42諫曰:「為治有體,上下不可相侵。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;今有人,使奴執耕稼,婢典炊爨43,雞主司晨,犬主吠盜,私業無曠,所求皆足。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,不復付任,形疲神困,終無一成。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?失為家主之法也。」孔明謝之。及顒卒,孔明垂泣三日。孔明曾經親自動手校核文書簿籍,主簿楊顒勸他道:「行政應當有體制,上下不應相侵犯。讓我給您以理家作譬喻:有一個人,叫手下的男工管耕田,女工管作飯,雞管報曉,狗管防盜,各自的職權不曠廢,要作的事都能作好。忽然一旦他要自己親身作這所有的事,不再把這些責任分交出去,精疲力竭,一件事也作不好。這難道是他智能不如傭工雞狗嗎?實在是因為失去作家主的原則了。」孔明對他表示歉謝。楊顒死後,孔明流淚了三天。
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,有才志,定公薦拔至侍御史。原性忠壯,好直言,定公時有得失,原輒諫爭,又公論之。人或以告定公,定公歎曰︰「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。」及原卒,定公哭之盡哀,曰︰「德淵,呂岱之益友,今不幸,岱復於何聞過哉?」此數君子者,所以能功名成立,皆由樂聞直諫,不諱過失故也。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44,有才志,定公薦拔至侍御史。原性忠壯,好直言,定公時有得失,原輒諫爭,又公論之。人或以告定公,定公歎曰:「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。」及原卒,定公哭之盡哀,曰:「德淵,呂岱之益友,今不幸,岱復於何聞過哉?」此數君子者,所以能功名成立,皆由樂聞直諫,不諱過失故也。呂定公有一個親近的人,叫徐原,有才能也有志向,定公推薦提昇他到侍御史。徐原性格忠耿,喜歡說直率話,定公有過失,徐原就提出反對意見和他爭辯,還在公共場合討論。有人告訴定公,定公歎息說:「這正是我重視德淵的原因。」徐原死後,定公哭祭他,極為悲哀,說:「德淵,是我呂岱的益友。現在不幸去世,我以後再從何處去聽到自己的過錯呢?」這幾位君子,其所以能成功立名,都因為樂於聽到直率的反對意見,不避諱自己的過失。
若其餘驕亢自用,不受忠諫而亡者,不可勝數;介甫多識前世之載,固不俟光言之而知之矣。若其餘驕亢自用45,不受忠諫而亡者,不可勝數;介甫多識前世之載46,固不俟光言之而知之矣。至於其他驕傲自恃,不接受忠告而失敗的人,簡直數不清,介甫對歷史的閱識很多,自然不必等光提出來說,您是都知道的。
孔子稱︰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,其恕乎?」《詩》云︰「執柯伐柯,其則不遠。」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,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,不遠求也。介甫素剛直,每議事於人主前,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,不少降辭氣,視斧鉞鼎鑊如無也。孔子稱: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,其恕乎?」47《詩》云:「執柯伐柯,其則不遠。」48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,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,不遠求也。介甫素剛直,每議事於人主前,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,不少降辭氣,視斧鉞鼎鑊49如無也。
孔子說: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,其恕乎?」《詩經》說:「執柯伐柯,其則不遠。」意思是說,應該以所希望於上級的態度對待下級,以所希望於下級的態度對待上級,不必另求法則。介甫素來很剛直。每次在皇上面前討論事情,就像和朋友在私下爭辯一樣,不肯稍稍婉轉語氣,對於王法威嚴完全不看在眼裏。
及之官,僚屬謁見論事,則唯希意迎合,曲從如流者,親而禮之;或所見小異,微言新令之不便者,介甫輒艴然加怒,或詬罵以辱之,或言於上而逐之,不待其辭之畢也。明主寬容如此,而介甫拒諫乃爾,無乃不足於恕乎?昔王子雍方於事上,而好下佞己,介甫不幸亦近是乎?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。及之官,僚屬謁見論事,則唯希意迎合,曲從如流者,親而禮之;或所見小異,微言新令之不便者,介甫輒艴然50加怒,或詬罵51以辱之,或言於上而逐之,不待其辭之畢也。明主寬容如此,而介甫拒諫乃爾,無乃不足於恕乎?昔王子雍方於事上52,而好下佞己53,介甫不幸亦近是乎?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。至於到辦公廳的時候,僚屬謁見討論事情,則只對那些揣摸意旨、迎合主張、滿口服從的應聲蟲加以親近優待;有的人意見稍有不同,微微提到新法令的不便,介甫就翻臉發怒,或是加以責罵折辱,或是啟稟皇上加以驅逐,不等人家把話說完。皇上對介甫如此寬容,而介甫對下級的反對意見如此拒斥,恐怕是不夠恕道吧?從前王子雍事奉主上很剛直,而卻喜歡下級對自己諂媚,難道介甫不幸也有類似的情形麼?這就是光所謂自信心太強的意思。
光昔者從介甫游,介甫於諸書無不觀,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。今得君得位,而行其道,是宜先其所美,必不先其所不美也。孟子曰︰「仁義而已矣,何必曰利?」又曰︰「為民父母,使民盻盻然,將終歲勤動,不得以養其父母,又稱貸而益之;惡在其為民父母也?」光昔者從介甫游,介甫於諸書無不觀,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。今得君得位,而行其道,是宜先其所美,必不先其所不美也。孟子曰:「仁義而已矣,何必曰利?」54又曰:「為民父母,使民盻盻然,將終歲勤動,不得以養其父母,又稱貸而益之;惡在其為民父母也?」55
光以前與介甫一同游處,介甫對各家的書無所不讀,而特別愛好孟子和老子的學說。現在得到君主信任,得到執政地位,來實行理想,應該說是先實行所贊美的東西,而不採取所不贊美的東西。孟子說:「仁義而已矣,何必曰利?」又說:「為民父母,使民盻盻然,將終歲勤動,不得以養其父母,又稱貸而益之,惡在其為民父母也?」
今介甫為政,首置條例司,大講財利之事;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,欲盡奪商賈之利;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,而收其息,使人人愁痛,父子不相見,兄弟妻子離散。此豈孟子之志乎?老子曰︰「天下神器,不可為也。為者敗之;執者失之。」又曰︰「我無為而民自化,我好靜而民自正,我無事而民自富,我無欲而民自樸。」又曰︰「治大國若烹小鮮。」今介甫為政,首置條例司,大講財利之事;又命薛向行均輸法56於江淮,欲盡奪商賈之利;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,而收其息,使人人愁痛,父子不相見,兄弟妻子離散。此豈孟子之志乎?老子曰:「天下神器,不可為也。為者敗之;執者失之。」57又曰:「我無為而民自化,我好靜而民自正,我無事而民自富,我無欲而民自樸。」58又曰:「治大國若烹小鮮。」59現在介甫執政,首先設置條例司,大講財利之事;又命令薛向在江淮地區實行「均輸法」,要想壟斷商業利潤;又派出使者到各地發青苗錢,收取利息,使人人悲愁痛苦,父子不相見,兄弟妻子離散,這難道是孟子的主張嗎?老子說:「天下神器,不可為也。為者敗之,執者失之。」又說:「我無為而民自化,我好靜而民自正,我無事而民自富,我無欲而民自樸。」又說:「治大國若烹小鮮。」
今介甫為政,盡變更祖宗舊法︰先者後之,上者下之,右者左之,成者毀之,矻矻焉窮日力,繼之以夜,而不得息;使上自朝廷,下及四野,內起京師,外周四海,士吏兵農,工商僧道,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,紛紛擾擾,莫安其居。此豈老氏之志乎?何介甫總角讀書,白頭秉政,乃盡棄其所學,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?今介甫為政,盡變更祖宗舊法:先者後之,上者下之,右者左之,成者毀之,矻矻60焉窮日力,繼之以夜,而不得息;使上自朝廷,下及四野,內起京師,外周四海,士吏兵農,工商僧道,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,紛紛擾擾,莫安其居。此豈老氏之志乎?何介甫總角讀書61,白頭秉政,乃盡棄其所學,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?現在介甫執政,完全改變祖宗舊法:在先的弄到後面,在上的弄到下方,在右的弄到左邊,已成的弄得毀滅,整天不停地努力,接着整夜不停地努力,使上自朝廷,下到四方,內起首都,外到遠地,士吏兵農,工商僧道,沒有一個人能保持原來生活,安守經常正道,紛紛擾擾,無人能安居樂業。這難道是老子的主張嗎?為甚麼介甫從小開始讀書,到頭髮白時執政,而竟完全拋棄所學,聽從現在那班膚淺人的主意呢?
古者,國有大事,謀及卿士,謀及庶人。成王戒君陳,曰︰「有廢有興,出入自爾師虞;庶言同,則繹。」《詩》云︰「先民有言,詢於芻蕘。」孔子曰︰「上酌民言,則下天上施;上不酌民言,則下不天上施。」自古立功建事,未有專欲違眾而能有濟者也。古者,國有大事,謀及卿士,謀及庶人。成王戒君陳62,曰:「有廢有興,出入自爾師虞;庶言同,則繹。」63《詩》云:「先民有言,詢於芻蕘。」64孔子曰:「上酌民言,則下天上施;上不酌民言,則下不天上施。」65自古立功建事,未有專欲違眾而能有濟者也。
在古時,國家有大事,朝野的讀書人與一般平民都被允許參加討論。周成王對君陳教訓說:「有廢有興,出入自爾師虞;庶言同,則繹。」《詩經》說:「先民有言,詢於芻蕘。」孔子說:「上酌民言,則下天上施;上不酌民言,則下不天上施。」自古以來立功勞建事業,從沒有違反眾議專行己意而能成功的。
使《詩》《書》孔子之言皆不可信,則已;若猶可信,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?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,而棄先聖之道,違天下人之心,將以致治,不亦難乎?使《詩》《書》孔子之言皆不可信,則已;若猶可信,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?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,而棄先聖之道,違天下人之心,將以致治,不亦難乎?如果《詩》《書》孔子的話都不可信則算了,如果還可信,那麼豈可都拋開不顧呢?現在介甫單只信幾個人的話,而拋棄先聖之道,違反天下人之心,要這樣能得治理,不也是很難嗎?
近者,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,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;而介甫遽倖倖然不樂,引疾臥家。光被旨為批答,見士民方不安如此,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,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。故直敘其事,以義責介甫;意欲介甫早出視事,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,以福天下。其辭雖樸拙,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。近者,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,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;而介甫遽倖倖66然不樂,引疾67臥家。光被旨68為批答,見士民方不安如此,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,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。故直敘其事,以義責介甫;意欲介甫早出視事,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,以福天下。其辭雖樸拙,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。
最近,地方大臣有人說發放青苗錢不對,皇上把他意見提執政大臣,而介甫立即惱怒不快,託詞患病,居家不出。光奉旨來批答這請假呈文,覺得士民正如此不安,而介甫竟要辭職而去,恐不是賢明的皇上予以重任的原意,所以直敘其事,以大義來責求介甫,用意是希望介甫早點恢復辦公,改變對人民不利的新法令,以造福天下;所批答的文辭雖然簡樸笨拙,但並無一字不合實情。
介甫不相識察,反督過之,上書自辨,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。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,然後乃出視事。出視事,誠是也;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,以慰安士民,報天子之盛德。今則不然,更加忿忿,行之愈急。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,詰責使之分析;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,劾奏乞行勘會。介甫不相識察,反督過之,上書自辨,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。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,然後乃出視事。出視事,誠是也;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,以慰安士民,報天子之盛德。今則不然,更加忿忿,行之愈急。李正言69言青苗錢不便,詰責使之分析;呂司封70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,劾奏乞行勘會71。介甫沒有認識這番意思,反而加以責備歸咎,上呈文自己辯護,以致皇上要親自作手詔來道歉,又使呂學士再三傳達其意,然後才肯出來辦公。出來辦公,自然是對的;可是應當儘速改正以前的錯誤法令,以慰安士民,報答皇上的大德。現在卻並不如此,反而更加忿怒,推行更急。李正言說青苗錢辦法不好,就加以盤問責難,要他自我檢討;呂司封報告說祥符知縣沒有發青苗錢,就上奏彈劾,請求加以會審。
觀介甫之意,必欲力戰天下之人,與之一決勝負,不復顧義理之是非,生民之憂樂,國家之安危,光竊為介甫不取也。觀介甫之意,必欲力戰天下之人,與之一決勝負,不復顧義理之是非,生民之憂樂,國家之安危,光竊為介甫不取也。看介甫的意思,似乎一定要努力和天下的人作戰,一決勝負,而不再顧及道理的是非、人民的憂樂、國家的安危。光為介甫着想,覺得不應採取這種態度。
光近蒙聖恩過聽,欲使之副貳樞府。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,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,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,進當今之急務,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,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。主上以介甫為心,未肯俯從。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,中外群臣,無能及者,動靜取捨,唯介甫之為信。光近蒙聖恩過聽72,欲使之副貳樞府73。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,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,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,進當今之急務,乞罷74制置三司條例司,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。主上以介甫為心,未肯俯從。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,中外群臣,無能及者,動靜取捨,唯介甫之為信。
光最近蒙皇上過獎,要任命作副宰相。光覺得居於高位的人不能無所貢獻,受大恩寵的人不能無所報答,因此又大膽提出去年的意見,提出當今的迫切任務,要求撤銷制置三司條例司,以及調回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。主上為尊重介甫的意見,沒有肯聽從。光私下想,主土對介甫的親信敬重,中外群臣沒有能趕上的;動靜取捨,都只聽信於介甫。
介甫曰可罷,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;曰不可罷,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。方今生民之憂樂,國家之安危,唯繫介甫之一言;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?夫人誰無過?「君子之過,如日月之食︰過也,人皆見之,更也,人皆仰之。」何損於明?介甫曰可罷,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;曰不可罷,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。方今生民之憂樂,國家之安危,唯繫介甫之一言;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?夫人誰無過?「君子之過,如日月之食:過也,人皆見之,更也,人皆仰之。」75何損於明?介甫說可以撤銷,則天下之人都受其恩惠;說不可以撤銷,則天下之人都受其損害。現在人民之憂樂、國家之安危,都在於介甫的一句話;介甫怎能忍心一定要順自己意思而不加顧侐呢?《論語》說:「君子之過,如日月之食:過也,人皆見之;更也,人皆仰之。」對其光明有何損失?
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,請罷條例司,追還常平使者,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,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;於介甫何所虧喪,而固不移哉?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,請罷條例司,追還常平使者,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,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;於介甫何所虧喪,而固不移哉?只要介甫能向主上說一句話,請撤銷條例司,調回常平使者,則國家太平之業都可以恢復舊觀,而介甫改過從善的美德比以前更加光大;這對介甫有甚麼損失,而要固執不肯改動呢?
光今所言,正逆介甫之意,明知其不合也。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,大歸則同。介甫方欲得位,以行其道,澤天下之民;光方欲辭位,以行其志,救天下之民︰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。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,以終益友之義。其捨之取之,則在介甫矣。《詩》云︰「周爰咨謀。」光今所言,正逆介甫之意,明知其不合也。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,大歸則同。介甫方欲得位,以行其道,澤天下之民;光方欲辭位,以行其志,救天下之民: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。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,以終益友之義。其捨之取之,則在介甫矣。《詩》云:「周爰咨謀。」76
光現在說的話,正違反介甫的意旨,明知道不相合。可是光與介甫取的方向雖異,最後目標則相同。介甫現在是要取得職位,以實行其理想,造福天下人民;光現在是要辭去職位,以實行其志向,拯救天下人民:這就是所謂「和而不同」。因此要向介甫陳述一下自己的意見和志向,盡一個益友的義務。《詩經》說:「周爰咨謀。」
介甫得光書,儻未賜棄擲,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;不可示諂諛之人,必不肯以光言為然也。彼諂諛之人,欲依附介甫,因緣改法,以為進身之資,一旦罷局,譬如魚之失水,此所以挽引介甫,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。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,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?孔子曰︰「巧言令色,鮮矣仁。」介甫得光書,儻未賜棄擲,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;不可示諂諛之人,必不肯以光言為然也。彼諂諛之人,欲依附介甫,因緣改法,以為進身之資,一旦罷局,譬如魚之失水,此所以挽引介甫,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。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,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?孔子曰:「巧言令色,鮮矣仁。」77介甫收到光這封信,如果並不予以拋棄,則請和忠實信義之士討論其可否實行,不可給諂媚阿諛的人看,他們一定不肯贊成光的意見的。那些諂諛之人,想依附介甫,以改變法制為緣由,而作為昇官發財的途徑;如果一旦停頓下來,就像魚失去了水;所以他們要拉着介甫,使介甫不能走平直的大道。介甫何必要遷就這般人的欲望,而不顧念國家的大計呢?孔子說:「巧言令色,鮮矣仁。」
彼忠信之士,於介甫當路之時,或齟齬可憎,及失勢之後,必徐得其力;陷諛之人,於介甫當路之時,誠有順適之快,一旦失勢,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。介甫將何擇焉?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,卒不得其死,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。雖然,於善人亦何憂之有?用是,故敢妄發而不疑也。彼忠信之士,於介甫當路之時,或齟齬78可憎,及失勢之後,必徐得其力;陷諛之人,於介甫當路之時,誠有順適之快,一旦失勢,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。介甫將何擇焉?國武子79好盡言以招人之過,卒不得其死,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。雖然,於善人亦何憂之有?用是,故敢妄發而不疑也。那些忠信之士,在介甫當政的時候,也許會提出些不同意見,令人討厭,但到失勢的時候,一定漸漸得到他們助力;諂諛之人,在介甫當政的時候,誠然造成恭順服從的快感,但一旦失勢,一定有出賣介甫以求自利的了。介甫將選擇何種人為友呢?以前國武子喜歡無保留地發表意見,揭出別人的過失,終於不得善終。光常常自苦與他相似,但仍改不掉這毛病。不過,對於一個善人說這些話,又何必有顧忌,因此敢於大膽妄言而不疑慮。
屬以辭避恩命,未得請,且病膝瘡不得出,不獲親侍言於左右,而布陳以書,悚懼尤深。介甫其受而聽之,與罪而絕之,或詬罵而辱之,與言於上而逐之,無不可者;光俟命而已。屬80以辭避恩命,未得請,且病膝瘡不得出,不獲親侍言於左右,而布陳以書,悚懼尤深。介甫其受而聽之,與罪而絕之,或詬罵而辱之,與言於上而逐之,無不可者;光俟命而已。
正因辭謝退避主上的任命,沒有能上朝謁見,而且膝上患瘡不得出門,無法親自到尊前隨侍進言,而以書面陳述意見,更加惶恐。介甫對於光,是接受聽從,還是加罪絕交,或是責罵折辱,還是啟稟皇上加以驅逐,都無不可;光聽候尊命而已。
導賞
本文主題是指陳王安石變法的錯誤,請求改正。全文結構可分為六大段。第一大段(至「為介甫一一陳之」)陳述作者要向王安石提出意見的原因和基本態度。第二大段(至「所謂用心太過者也」)先提出王安石的兩大缺點:用心太過,自信太厚;然後就第一點缺點加以論證發揮。第三大段(至「所謂自信太厚者也」)就第二點缺點加以論證發揮。第四大段(至「不亦難乎」)指陳王安石的變法,與孟子、老子的主張不合;不採納民意,與儒家主張不合。第五大段(至「為介甫不取也」)指陳王安石剛愎自用,抗上凌下的不良態度。最後第六大段重覆表明主張,請王安石採納,並暗示如果他肯採納,則作者可竭誠合作,否則即分道揚鑣。
司馬光是一位正統派的儒家人物,學養很深,本文措詞語調,大體也保持很好的儒家風度。但也許因為當時政見爭執很激烈,因此態度中也有暗藏火氣之處,例如:「人人歸咎於介甫,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?……」等於說王安石不知天下情況,失於明察;「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,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。」等於說王安石只責備別人,不肯自省。「自以我之所見,天下莫能及……」等於說王安石驕傲自大。「何介甫……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?」等於說王安石成為追求財利的小人。「觀介甫之意,必欲力戰天下之人,與之一決勝負,不復顧義理之是非,生民之憂樂,國家之安危。」等於說王安石賭氣蠻幹,不講道理。「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,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?」等於說王安石遷就小人私慾,不顧國家利益。「彼忠信之士……介甫將何擇焉」一段,以王安石個人利益為言,等於說你和他們作朋友,一定對你不利;與我們作朋友,對你有利。
以上這些話所表現的態度,都是令人難於接受的。基本上說來,司馬光無意中犯了一個大毛病,即是不夠「恕道」。他沒有推己及人,站在王安石的立場,推想王安石的心情、動機和理由;而只講他自己單方面的道理。他對王安石既不夠了解,因而就不能諒解。
平心而論,王安石並非不知天下情況,並非不曾自省,並非世俗的驕傲自大,並非單純追求財利的小人,並非賭氣蠻幹、不講道理,並非遷就小人私慾、不顧國家利益,並非以他個人利益為重。司馬光所指陳的這些缺點,只是就表面來觀察,言之成理,但失於過份。王安石的基本動機是忠心耿耿要改革政治,復興國家。司馬光本文前一部份承認這一點,但到後一部份就否定了王安石的基本動機;這樣當然談不攏。王安石設計的新政策,本身都有其理由,有其優點;司馬光不從這方面去討論,只籠統地說它與儒家道家主張不合;使人民受苦,詳細原因何在,他也沒有說清;又沒有提出建設性的改良意見,只是要求王安石取消新法,使人民「襲故守常」,使「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」!問題是,當時宋朝貧弱,用「清靜無為」「守祖宗舊法」不能復興國家。這種主張,王安石當然不肯接受。司馬光和他同時的儒家正統派諸人,都犯了這一毛病:不諒解王安石的動機,不虛心討論他新政策的理由。
查閱次數:868
資料來源:
朗讀:黃健偉(粵)、程廣寬(普)
|
註釋、譯文:《友聯活葉文選》,友聯出版社
|
導賞:《友聯活葉文選》,友聯出版社(文)、黃健偉(粵)、程廣寬(普)
作者/出處
司馬光
司馬光,生於宋真宗天禧三年,卒於宋哲宗元祐元年(一〇一九──一〇八六)。字君實,陝州夏縣(今山西夏縣)人。幼聰穎,七歲已愛讀《左傳》。宋仁宗寶元二年(一〇三九)進士,初任奉禮郎、翰林學士、御史中丞,歷任直秘閣、開封府推官,神宗即位,任知永興軍、西京留守御史臺。任御史中丞時,倡導仁政,反對王安石變法。哲宗即位,任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。為相八個月,卒於任上。追贈溫國公,謚文正。
司馬光是北宋著名史學家與政治家。所編撰的《資治通鑑》二百九十卷,上起周烈王二十三年,下訖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(西元前四〇三──九五九),記事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。此書得神宗賜名,並親作序文,以其「鑑於往事,有資於治道」,故名《資治通鑑》。全書按年月排列,參考淵博,鑑別精確,文字明暢,是中國編年史的巨著。另著有《司馬文正集》八十卷,《涑水紀聞》十六卷。
查閱次數:4274
資料來源:
《中國文學古典精華》,商務印書館(香港)有限公司
創作背景
介甫,是王安石(一〇二一──一〇八六)的字。司馬光給王安石的這封信,大約寫於一〇七〇年,時司馬光五十二歲,王安石五十歲。那時司馬光是諫議大夫,王安石是宰相。這是當時「變法」政爭的一個重要文獻。要了解這篇文章,我們必須先了解那一段歷史背景。
又,王安石接到這封信後,曾有《答司馬諫議書》,讀者可參閱。
資料來源:
《友聯活葉文選》,友聯出版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