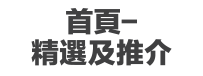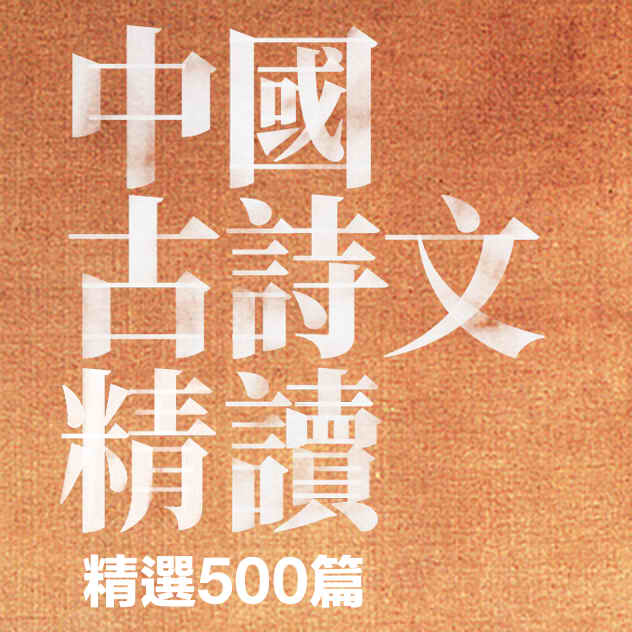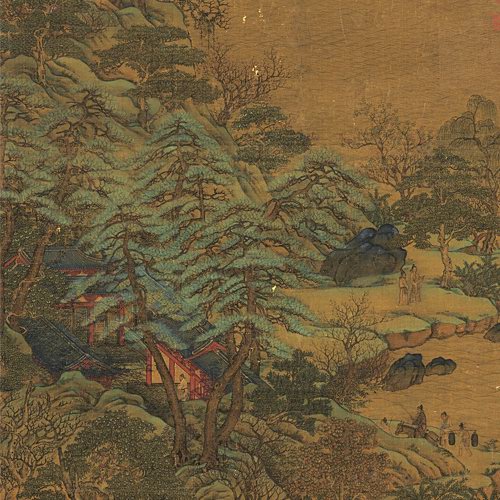文選序
式觀元始,吵覿玄風。冬穴夏巢之時,茹毛飲血之世,世質民淳,斯文未作。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,始畫八卦,造書契,以代結繩之政,由是文籍生焉。《易》曰︰「觀乎天文以察時變,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」文之時義遠矣哉!式觀元始,吵覿玄風1。冬穴夏巢之時,茹毛飲血之世,世質民淳,斯文未作2。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,始畫八卦,造書契,以代結繩之政,由是文籍生焉。《易》曰:「觀乎天文以察時變,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」3文之時義遠矣哉!
我們看上古,可以遠遠看出歷史早期的情況。當人們冬天住在地穴裏,夏天在樹上結巢的時候,是質樸時代,人都很樸厚,文學還沒有興起。到了伏羲為王的時代,開始畫八卦,造出書契來記事,代替從前結繩記事的辦法,由此,文籍發生了。《易經》上說:「觀乎天文,察時變,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」;文的歷史意義確實很大了。
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,大輅寧有椎輪之質;增冰為積水所成,積水曾微增冰之凜。何哉?蓋踵其事而增華,變其本而加厲;物既有之,文亦宜然。隨時變改,難可詳悉。若夫椎輪為大輅4之始,大輅寧有椎輪之質;增冰5為積水所成,積水曾微增冰之凜。何哉?蓋踵其事而增華,變其本而加厲;物既有之,文亦宜然。隨時變改,難可詳悉。大輅是從簡陋的無輻的輪子進步而來,大輅的性質與無輻的車輪卻不同;厚厚的冰是積水而漸漸形成的,開始的積水卻並沒有厚冰那種寒冷。是甚麼原因?只因為一切事接續發展,便愈來愈豐富,改變了原先的樣子,便有加強的新效果;物是如此,文章也是如此。都是隨着時代而變化改易,很難詳細弄明白演變過程。
嘗試論之,曰︰《詩序》云︰「時有六義焉︰一曰風,二曰賦,三曰比,四曰興,五曰雅,六曰頌。」至於今之作者,異乎古昔,古詩之體,今則全取賦名。荀、宋表之於前,賈、馬繼之於末。自茲以降,源流實繁。述邑居,則有憑虛亡是之作,戒畋游則有長楊羽獵之制。若其記一事,詠一物,風雲草木之興,魚蟲禽獸之流,推而廣之,不可勝載矣。嘗試論之,曰:《詩序》6云:「時有六義焉:一曰風,二曰賦,三曰比,四曰興,五曰雅,六曰頌。」至於今之作者,異乎古昔,古詩之體,今則全取賦名。荀、宋7表之於前,賈、馬8繼之於末。自茲以降,源流實繁。述邑居,則有憑虛亡是9之作,戒畋游則有長楊羽獵10之制。若其記一事,詠一物,風雲草木之興,魚蟲禽獸之流,推而廣之,不可勝載矣。
我曾經試作討論如下:《詩序》上說,「詩有六義焉,一曰風,二曰賦,三曰比,四曰興,五曰雅,六曰頌」。到現在的文人,情形又與古時不同。古詩以賦為一種表現法,現在則把本來屬於古詩的都名之為賦。荀卿與宋玉揭發於前,賈誼、司馬相如承繼於後。再下來,發展源流非常繁雜。講都會山川的有《兩京賦》中借憑虛公子談話的寫法,和《子虛賦》《上林賦》中借亡是公談話的寫法;勸戒君王田獵的有《長楊》《羽獵》等賦。至於那些記一件事,詠一個東西,或者對風雲草木的感興,對魚蟲禽獸的描寫,諸如此類,更是說不完了。
及楚人屈原,含忠履潔,君匪從流,臣進逆耳,深思遠慮,遂放湘南。耿介之意既傷,壹鬱之懷靡愬。臨淵有《懷沙》之志,吟澤有憔悴之容。騷人之文,自茲而作。詩者,蓋志之所之也,情動於中而形於言。《關睢》《麟趾》,正始之道著;桑間濮上,亡國之音表。故風雅之道,粲然可觀。及楚人屈原,含忠履潔,君匪從流11,臣進逆耳12,深思遠慮,遂放湘南。耿介之意既傷,壹鬱13之懷靡愬。臨淵有《懷沙》14之志,吟澤有憔悴之容。騷人之文,自茲而作。詩者,蓋志之所之也,情動於中而形於言。《關睢》《麟趾》15,正始16之道著;桑間濮上17,亡國之音表。故風雅之道,粲然可觀。在楚國的屈原,以一個心志忠誠而行為高潔的人,卻碰上君王不能納諫,而臣子勉強進言的境遇,結果弄得流放到湘水之南,屈原孤介的心意受了傷害,抑鬱的情懷無處發洩,在水邊有《懷沙賦》所表示的意向,在大澤旁高吟弄成憔悴的樣子。於是就有了述感傷的騷體文。詩本來是表示志的方向的,內心有所感便表現在語言中。像《關睢》《麟趾》各詩,是糾正風俗之作,像桑間濮上諸詩,是表現亡國之音;在那個階段中,文學的光芒很盛。
自炎漢中葉,厥塗漸異。退傅有在鄒之作,降將著河梁之篇,四言五言,區以別矣。又少則三字,多則九言,各體互興,分鑣並驅。頌者,所以遊揚德業,褒讚成功;吉甫有穆若之談,季子有至矣之歎。舒布為詩,既言如彼;總成為頌,又亦若此。次則箴興於補闕,戒出於弼匡;論則析理精微,銘則序事清潤;美終則誄發,圖像則讚興;自炎漢中葉,厥塗漸異。退傅有在鄒之作18,降將著河梁之篇19,四言五言,區以別矣。又少則三字,多則九言20,各體互興,分鑣並驅。頌者,所以遊揚德業,褒讚成功;吉甫有穆若之談21,季子有至矣之歎22。舒布為詩,既言如彼;總成為頌,又亦若此。次則箴興於補闕,戒出於弼匡;論則析理精微,銘則序事清潤;美終則誄發,圖像則讚興;自漢朝中葉以後,途徑又不同了。韋孟以退職的太傅身分,作出在鄒地閒居時的詩,李陵以降將的身分,作出「攜手上河梁」的詩;四言五言,便分開了。此外,詩句的字數少的有三字,多的有九字,各種體裁興起,分頭發展。頌則是稱讚表揚人的德性事業和功績的,尹吉甫有讚美周宣王的詩,吳季札有讚美魯樂的頌。發揮成詩,就是上面所說的;合起來當頌看,就是這樣了。其次箴是勸人改過的文字,或是糾正君王的過失的文字;論要能將道理分析到精微之處,銘要能將敘述寫到清明圓潤的地步;在人死後作贊美就有了誄,對於圖像作題跋就有了讚。
又詔誥教令之流,表奏牋記之列,書誓符檄之品,弔祭悲哀之作,答客指事之制,三言八字之文,篇辭引序,碑碣誌狀,眾制鋒起,源流間出。譬陶匏異器,並為入耳之娛;黼黻不同,俱為悅目之翫。作者之致,蓋云備矣。又詔誥教令之流,表奏牋記之列,書誓符檄之品,弔祭悲哀之作,答客指事之制23,三言八字之文,篇辭引序,碑碣誌狀,眾制鋒起,源流間出。譬陶匏24異器,並為入耳之娛;黼黻不同,俱為悅目之翫。作者之致,蓋云備矣。此外,詔誥教令等等,表奏牋記等等,和書札、誓詞、檄文、祭文之類的作品,隱語式的作品,以及辭與序,碑文與行狀,種種體裁起來,源流非常間雜。就好像音樂有許多種,服飾有許多種一樣,作文章的也有許多種,可以算齊全了。
余監撫餘閒,居多暇日,歷觀文囿,泛覽辭林,未嘗不心遊目想,移晷忘倦。自姬漢以來,眇焉悠邈,時更七代,數逾千祀。詞人才子,則名溢於縹囊;飛文染翰,則卷盈乎緗帙。自非略其蕪穢,集其清英,蓋欲兼功,太半難矣。若夫姬公之籍,孔父之書,與日月俱懸,鬼神爭奧;孝敬之准式,人倫之師友;豈可重以芟夷,加之翦截?余監撫25餘閒,居多暇日,歷觀文囿,泛覽辭林,未嘗不心遊目想,移晷忘倦。自姬漢以來,眇焉悠邈,時更七代26,數逾千祀。詞人才子,則名溢於縹囊27;飛文染翰,則卷盈乎緗帙28。自非略其蕪穢,集其清英,蓋欲兼功,太半難矣。若夫姬公之籍,孔父之書,與日月俱懸,鬼神爭奧;孝敬之准式,人倫之師友;豈可重以芟夷,加之翦截?
我在以太子身分執行職務而有閒的時候,就遍讀各種文章,常常想着,看着,過許久時間忘記了困倦。周漢以來,時間已經很長,換了七個朝代,超過一千年。成功的文人,好的文章,書上記載的都很多。自然非得淘汰掉較劣的一部份來留下較好的一部份不行,不然要弄好就很不容易。如周公、孔子的著作,那是像日月一樣長在,像鬼神一樣深奧;所論是人倫規範,豈能加以刪節截取?
老莊之作,管孟之流,蓋以立意為宗,不以能文為本;今之所撰,又以略諸。若賢人之美辭,忠臣之抗直,謀夫之話,辨士之端,冰釋泉涌,金相玉振;所謂坐狙丘,議稷下,仲連之卻秦軍,食其之下齊國,留侯之發八難,曲逆之吐六奇,蓋乃事美一時,語流千載;概見墳籍,旁出子史,若斯之流,又亦繁博,雖傳之簡牘,而事異篇章;今之所集,亦所不取。老莊之作,管孟之流,蓋以立意為宗,不以能文為本;今之所撰,又以略諸。若賢人之美辭,忠臣之抗直,謀夫之話,辨士之端,冰釋泉涌,金相玉振;所謂坐狙丘,議稷29下,仲連之卻秦軍30,食其之下齊國31,留侯之發八難32,曲逆之吐六奇33,蓋乃事美一時,語流千載;概見墳籍,旁出子史,若斯之流,又亦繁博,雖傳之簡牘,而事異篇章;今之所集,亦所不取。像老子,莊子,管子,孟子的書,都是以意為主,不重在文章;現在我在文選中也畧掉。至如賢人所說的有價值的話,忠臣的直諫,或者定謀的人、辯說的人的言論;都是暢快有力,像金玉一樣可貴。像人所說的:田巴在狙丘地方的論辯,在稷下的議論;魯仲連拒退秦軍的說詞;酈食其對齊國的說詞;張良反對立六國後的八難議論;陳平的六種奇計等等,都是當時為人所贊美,後世也永久流傳的,都可以在經籍、子書、史書裏找到。這一類東西很多,雖然記載下來,但與尋常文章性質不同。現在所收的也不包含這些。
至於記事之史,繫年之書,所以褒貶是非,紀別異同,方之篇翰,亦已不同。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,序述之錯比文華,事出於沈思,義歸乎翰藻,故與夫篇什,雜而集之。遠自周室,迄於聖代,都為三十卷,名曰《文選》云爾。至於記事之史,繫年之書,所以褒貶是非,紀別異同,方之篇翰,亦已不同。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,序述之錯比文華34,事出於沈思,義歸乎翰藻35,故與夫篇什,雜而集之。遠自周室,迄於聖代36,都為三十卷,名曰《文選》云爾。至於記事體、繫年體的歷史著作,本來是用以對是非作判斷,紀敘各種說法的;與文學作品比較,也已經不同。可是史書中的贊、論、序、述等等,都有豐富的文學成分,有思想,有詞藻;所以也和其他文學作品一樣,收集一些。遠自周朝起,直到本朝為止,一共三十卷,題名就稱作《文選》。
導賞
昭明太子編《文選》後作這篇序,目的在說明他自己對文學源流的看法,和選文的標準。因此全文主旨就是講文學之發展,並說明他選文時不選那些著作和材料。講這兩點都沒有多少理論成分,只是直述他自己的看法和選法。第一段,說「文」之發生。主要意思是說明文學有種種變化:由簡至繁。
第二段,歷述各種文體之起源及發展。其中所舉出的賦、騷、詩、頌、箴、戒、論、銘、誄、讚……等等體裁,比陸機《文賦》裏所舉的十體複雜得多;但解釋時所用的字句,如用「精微」描寫「論」,用「溫潤」描寫「銘」,則都與《文賦》同。又「三言八字之文」,是指隱語說,「三言」如《國策》中的「海大魚」,八字如「黃絹幼婦外孫齏臼」。這種隱語式的作品,可以獨成一體。有人解為三言八言的詩;但看本序中論詩是在前面;這裏所說的當然不是詩,舊說恐誤。
第三段歸到自己編《文選》上說。主要表明自己選文是取文學觀點。
查閱次數:644
資料來源:
朗讀:黃健偉(粵)、白雪蓮(普)
|
註釋、譯文:《友聯活葉文選》,友聯出版社
|
導賞:《友聯活葉文選》,友聯出版社(文)、黃健偉(粵)、白雪蓮(普)
作者/出處
蕭統
蕭統(公元五○一——五三○),字德施,小字維摩。他是南北朝時梁武帝的長子;天監中立為皇太子。性仁孝,工詩文,喜結納名士,極負時望。先梁武帝卒,謚「昭明」,故稱「昭明太子」。所作詩文有專集;所編「文選三十卷」,後世稱《昭明文選》,為今存文人總集最早的一部書;此外,還編有《陶淵明集》,也是中國文人專集的第一部。
查閱次數:432
資料來源:
《友聯活葉文選》,友聯出版社
創作背景
本文是昭明太子蕭統自己給他所編的《文選》寫的序文。這部《文選》的選文標準是純文學標準;所以不選「經」「史」「子」,而只限於文學作品。
這篇序文敘述蕭統自己對文章源流的看法,和他選文的標準,有敘有議。
資料來源:
《友聯活葉文選》,友聯出版社